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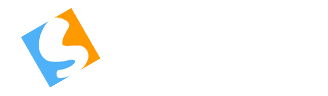
第19届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

《梦的拜访》导演:王淞可
@第19届FIRST西宁青年电影展 主竞赛单元

|前言
《梦的拜访》讲述了三位并不相互认识的角色,徐博、李可以及老王,三个人在三天内独自掌握了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一天”的故事。他们因为偶然经过彼此,又因为必然陷入了他们各自忧虑的情感。
的确,这样的故事结构与叙事态度,总是会令我们在其表层风格中,将《梦的拜访》误认为是一部洪常秀式的电影。但笔者恰恰反对这一类过时了的,且粗暴的评论——正如同大量的评论随意地将洪常秀、张律以及滨口龙介放在一起相比较,这样愚蠢的讨论令我以为他们是否真的看过这些作者的电影——事实上,王淞可的电影区别于任何一位我们已知的作者。
当我们轻易断言,一位作者的电影是“谁谁谁式”的,仿佛那是在说,他没有采取任何可能的实施努力的路径,而仅是在偷取其它作者的过往的成果。然而,我想直接断言,王淞可是我今年在FIRST影展主竞赛所见过的最勤奋的作者。当我说这句话时,我并不是在提及他为这部电影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和金钱(事实上在看到《梦的拜访》之前,我几乎对这位作者一无所知),而是指,他对人物的反复思考,对生活的并不轻易地体察,以及拒绝草率地挪用大量的造型(今年看了太多这样的电影)。仅是从这一点上看,他便已经是一位我们值得尊重和给予些许赞扬的作者了。

《梦的拜访》剧照
|情感诞下我们
我在想,我们共同的事物。我在想彼此和遥远。我在想我与你是否有着像夜与日一般的距离。我在想日子应当同影子一般总是与我们毫无关系却相伴我们永恒。我在想,在我遇见你之前,又是什么提前认识了我......
无论如何形容,这些都曾、也必将是《梦的拜访》的主题:那是电影对我们的一次深切的同情,一种体面但忧郁的诉说,它(像一位过于早熟的孩子)轻轻告知我们,不再是我们发觉了情感,而是情感诞下了我们。
《梦的拜访》始终是一次呢喃。这意味着,一位忧愁的旅人总是无法准确辨认他口中吐露的事物是否具体,因为他专注的永远是那嘟囔的口型带来的哀伤的姿态。一位呢喃的人说了什么并不重要,当他开口,我们便活在了他难隐的悲哀里。就像《梦的拜访》似乎不存在任何的某个“故事”——一部电影又何必关乎于一个故事?——它只存在写作。有时候,一些优良的作者并不在乎太多纸面上的内容,而选择专注于笔尖的运动和自己的坐姿。
佩措尔德的新作《镜的第三乐章》是一个良好的例子。开场,佩措尔德拍摄了一系列葆拉·贝尔挂满愁容的面庞以及她的视线,仿佛有什么过去的事物牵绊着她;结尾,她再次看向家里的角落,脸上闪过一抹“迟来”的笑容,仿佛她重新认识了这个房间。对视线的描绘和体察,即是佩措尔德的写作方式。在他的电影内,佩措尔德的首要任务便是将人们的视线成功组织起来,并在往后的时间拍摄视线的疑虑、轻抚,和它们之中饱含的情感。

《镜的第三乐章》剧照
但王淞可,这位我们身边“姗姗来迟”的新的作者,于他而言,写作则是指那些电影主动“分心”的时刻,是伏案写作时惯用的右手因为情感霎那时的涌出而止不住的颤动。王淞可和佩措尔德的影像共同指出,电影或许仅被允许存在数个闪烁的、模糊我们的姿态和视线,紧接着如何宽慰它们,引见(正如同洪常秀电影那傲然的片名!)它们之中的“低眉”,即是电影需要完成的一次写作的任务。
我们看到,六位角色、三对关系以剪影的姿态被“修正”在三扇窗户面前,他们依照自己的心情描述各自的情感,但,真的是这样吗?情感是能够被我们准确描述的吗?因为紧接着,在每一段故事即将临别的末尾,我们看到了情感是如何先一步伫立在那里,伫立在了影像的深处。

《梦的拜访》剧照
徐博一个人倚靠在墙上抽起人生里的第一根烟,静静偷听着喜欢的女孩演奏的钢琴曲,李克提着行李箱经过,紧接着,是一个缓慢的变焦推镜,我们注视着女孩远去,揣测她的背影,目光跟随摄影机试图“跟”上她,抵达她,但,有什么事物要比我们,要比摄影机先一步推走了她。那是某个“别人的”音乐。

《梦的拜访》剧照
当然,在那一个镜头里我们总是不得不承认有那么的一瞬间的确看见了洪常秀,目睹了他的《草叶集》的精神是如何再一次地降临在《梦的拜访》:音乐取消了区分我们的一切事物。又或者,我也可以说,情感取消了区分我们的一切事物,因为那正如同充盈的空气一般被我们平均地分享。

《草叶集》剧照
如果说在《草叶集》内,我们明晰了洪常秀那真正的精神——只有当目光确实汇集在表面时,人们才能领悟到奇妙之处,而这种奇妙常常正是那些最为内在的事物在交叉时发出的闪光。那么在《梦的拜访》,当我们的目光终于“跨越”了那一步,“跃入”音乐带来的时刻,音乐塑造的情境,那一刻,我们才姗姗发觉情感之于两位陌生的人之间的不可分割。那既是一则故事的结尾,也是一段关系的开头。
因此,赞扬王淞可正如同我们总是赞扬生活里那些秘密的交叉,作为《梦的拜访》的作者,他并不着迷于叙事带来的游戏,编排一个令观众惊呼的结构,而选择坦然地拥抱情感,接受事物之外的事物是如何引导我们重新遇见彼此。不同的人,不同的过去,甚至相异的情感,但共同的音乐必须在同一刻在我们的内心里“振聋发聩”,那是因为它就在那里。

《梦的拜访》剧照
稍晚的故事里,我们又看到了一出“临别的开场”:李可与李可如在互相拥抱后道别,李可乘坐电梯沉默地离开了画面,紧接着,老王怀着某种愧疚的心情跑回酒店(甚至因为自动门的存在,他的脚步出现了短暂的“滞空”)。在这样的一场戏内,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某种祝福的动作,那是一次拥抱,一个短暂的告别,一位女孩再次拜访多年未见的朋友,却仅凭某个“梦的证据”。两人在相同的夜里互相梦见,并彼此祝福(那是怎样的善良),随后,情感因为梦的出现自然而然地降临,又因为虚构的侵入而确立人们在彼此内心的位置。
于王淞可而言,梦可能从来不是一个文本意义上的事物,而是一个写作的姿态、一个插入虚构的方式——这并不新鲜,阿彼察邦、洪常秀、雅克·里维特、大卫·林奇、张律,甚至糟糕的塔西姆·辛都曾拍摄过梦境,且在其之上组织了他们自己的虚构,但,在王淞可的虚构内,李可和李可如行走在街上聊到梦里的蜜蜂......那是一个令人心碎的跟拍镜头,在李可如(还有我们)听闻李可对她过去生活的悼念时,电影什么都不说,它保持沉默,只是去看,仿佛一位出于礼貌而用目光简单照顾我们的内向的身旁的朋友。
也因此,在王淞可的梦的虚构的写作内,情感总是先一步提起它的笔尖。在一个有些安静的镜头里,老王矗立在酒店门口等人,下一个镜头拍摄的则是李可的视线。电影没有解释什么,但我们知道情感沾染了二者,我们很难说电影在这一刻认同了李可和老王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这不是一个正反打镜头),但我们几乎可以断言,电影在这一刻肯定了情感勾连二者生命经验的能力。

《梦的拜访》:李可的目光里,酒店门口等人的老王
电影的结尾,老王给松松发去了一条语音——又是一次告别——他得知昨晚梦见的那位老人于今早(在他睡醒后不久)刚刚过世。他没说太多的话,只是简单安慰了对方,便背着行囊离去......突然,我们的目光在那一刻并没有跟上他的步伐。那是一个横摇镜头,我们看见了老王先一步离开了这个画面/情境,以为电影又将回归它的黯然神伤,但过了一会儿,仿佛摄影机方才反应了过来,又将我们的视线摇了过去,跟随上了老王的步伐。似乎,那是在尝试着去拉扯住他、挽留住他,又似乎,正如同加瑞尔的《北斗七星》里死去的父亲在梦里突然地走进房间,除了简单的慰问我们毫无办法。但那怎么能说我们毫无情感?情感就在那里,犹如那个奇妙的摇镜,我们一转身才发觉与它撞了个满怀。
这三则故事结尾,或许,也是三个别开生面的新的开始。但无论如何,它们皆表明了情感是如何诞下我们的。它早已在那里等候着我们。在有些时候,我又会想到皮亚拉的《梵高》。梵高死去之后,与此同时有一位女工脚被砸了一下,就好像梵高和女工作为两类陌异的电影内的图像都仅是世界的一部分,它们自如地运转,试图不干涉彼此的结论,但更多的,那也是我们情感的一次“分心”。

莫里斯·皮亚拉《梵高》剧照
皮亚拉将梵高死去的悲苦转移至了世界的角落,他(指作者)分心了,他不忍直视那个人的死亡,于是乎,他选择将目光望向同样的悲苦——脚被砸了一下的疼痛和死亡又有什么不同!它们皆是某种令我们潸然泪下的,踌躇的事物。
那么,我想到,朱老师的悲苦又与餐馆里的师傅的劳动,又有什么区别;徐博的难言之隐又与小区楼底下玩耍烟火的孩童的喜悦又有什么区别。简单的剪辑,两种图像在公正的情感面前被放在一起讨论。没什么其他的意思,因为情感就是情感,它不会因被剥夺了某些事物就逊色一分也不再由于添加了一处赘笔便浓重许多。

《梦的拜访》剧照
也因此,我想说,《梦的拜访》的美丽之处永远在于它影像层面的澄澈,那会令我们想起每天晨起的日出,它有在说什么吗?太阳有在说什么吗?没有,我们只发觉自己是幸福的,因为我们正被如此强烈的事物包裹着。
某一些时刻,这部电影对待情感正如同它如何对待那些半夜失眠的人们。几位我们方才认识的角色,他们只是坐在床沿,然后我们便什么都说不来了。因为我们将要离开他们,因为情感即将诞下我们。
|专访王凇可

被偶然看到
采访 / 唯唯
受访 / 王淞可
排版 / emf
责编 / 阿崽、emf
制图 / 阿崽
左:异见者编辑部
右:王淞可
在今年入围FIRST主竞赛的导演中,您的身份很特殊。您不仅是导演,还是一位影评人和电影学者。因此,除了《梦的拜访》这部电影,我们更想聊聊电影与您之间的关系,以及您对电影的态度。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写作对您究竟意味着什么?以《梦的拜访》为例,您是如何完成它的写作的?

我的身份确实比较多,但都围绕着电影,所以也不算跨界。只是有时会感到思维上的疲惫,因为需要在不同领域的思维方式间转换。但无论是做研究、策展,还是创作,都是出于热情和兴趣。对某些点感兴趣,我就会想去做研究,这又可能关联到策展,因为策展与学术研究相关,希望能让更多人看到这些东西。
创作,如你所说,源于写作的习惯,我也有记录的习惯。我本科读的是广播电视编导,偏向实践。当时高考,我本该走文化课的路子,但我就是喜欢电影。那时对电影学院的门类不太了解,恰好我父亲是高中班主任,他班上有些学生学广电编和电影。他并不排斥艺术,不像其他家长那样,反而很支持我,所以我高考就选择了这个专业。记得当时他班上有个男孩,现在回想起来很神奇,我们聊天时,他说他想去南加大学导演。那时我虽然懵懂,但我们看的电影却有重合。比如我当时很喜欢台湾新电影之后的蔡明亮,还有钟孟宏的《停车》[2008],以及深田晃司的作品。能在那个时候碰到一个能聊艺术电影的大哥,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因为这种实践类的学习背景,我从未放弃过实践的尝试,经常零成本地用手机或相机拍些东西。还有只要有兴趣我就会写点东西,不过现在影评写得相对少了,只为自己特别感兴趣的片子写。人的精力会慢慢缩减,不像上学或更年轻时时间那么充裕。三十岁之后,感觉会慢慢分清主次,要做的事可能会更突出一些。其实我也没太想清楚,但创作应该会一直做下去。做艺术或做电影就像一个永远的囚笼,你会不断地思考,无法控制或停下来。当你思考一个事,或者觉得它好玩,你就会想把它做出来,区别只在于什么时候做,以及做成什么样。
在您看来,写影评和您的电影创作之间有怎样的联系?此前的影评工作是否帮助了您后来的创作?
我觉得写影评对创作有帮助,因为它是一个厘清自己思路的过程,尤其是为你特别感兴趣的东西而写的时候。当然,有些影评不一样,如果不是出于个人兴趣或研究目的,效果就不同。我并没有在专业领域系统地研究过影评。要做好评论,需要有自己的系统和生态,就像法国《电影手册》那批影评人一样,他们有自己的脉络,但我在这方面研究不深。
我只是会对某些影片深入研究,比如我确实写过关于洪常秀的一些评论。还有侯麦,我曾用一个暑假看完了他所有的片子,都特别喜欢,于是就边看边写,最后形成了一系列关于侯麦的评论。但我写完影评后,自己很少会再去看。写的过程中会不断地读,但完成后就羞于再看了。它帮我记录了某一时间的感受和想法,梳理了一些线索,比如洪常秀的那些特点及其背后的脉络,我都研究过。我尤其喜欢他近期的作品,从《引见》[인트로덕션, 2021]之后,那些他自己掌控力特别强的片子,我都非常欣赏。

인트로덕션 (2021)
无论是您在学习期间的影像记录,还是后来的影评写作,您似乎都习惯于将日常事物记录下来,并融入创作。但在《梦的拜访》中,我们发现除了对日常的考察,您还融合了大量的虚构与思考。比如电影里提到的“梦”,并非指谁做了什么梦,而是一种介入虚构的方式。您如何看待和平衡虚构与现实之间的比例,又如何去平衡两者?
是的,我确实经常在日常与虚构之间做平衡和取舍。我确实是很关注日常,想记录日常,但又想做一些戏剧性的东西,感觉像是在一种艺术形式和一种日常纪实之间摇摆。我最早剪辑的版本很长,有160分钟,之后剪到120分钟,再到108分钟。片子长的时候,记录性或日常景观的部分会更多。
我努力平衡的一点是,不希望电影变得无法进入。我希望观众还是可以进入一个故事或虚构中,从而认识到日常的荒诞性。它其实更像小说,我很喜欢雷蒙德·卡佛和凌叔华的小说,他们的作品读起来有一种忧郁的氛围,能通过日常的街道和景观唤起。但这种被唤起的情感因人而异,且与特定时间相关。我也很喜欢慢电影,或者说那种节奏缓慢、能唤起思考的电影,但我相信它们的组建方式更艺术化,或许在美术馆等场域更能唤起观众的感官,但我不确定每个人都能同频。

所以在这部电影里,我希望它有一条线索。我最初写的是故事,而非纯粹的情绪,希望通过故事让景观唤起情绪。比如,如果对着窗外的街道发呆,每个人的想法都会不同。但如果前面有一个事件,比如一个失恋的人坐在这里,再带入一些情绪,或用绘画、文字等媒介介入,这条街道和日常景观就会变得暧昧,能引发更多联想。
就是在这两者间不断平衡,剪辑了很多版本,最终才定格在72分钟。我给一些朋友看,后来也请教了黄骥导演和杨超导演,ta们都认为70多分钟是比较合适的体量。所以我在景观氛围、人物情绪和事件之间不断取舍。当然,我也不确定这个平衡是否做得足够好,因为我的创作一直没有在大银幕上检验过,这也是一个不断探索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的过程。
对我而言,《梦的拜访》的一大核心主题关乎情感。电影里有三组人物,其中一个镜头是三个人在同一个夜晚,您拍摄了ta们在床边的姿态。这几乎指向了影片的核心:无论这三个人身处何方,情感是ta们共通的。ta们有共同的情感,或悲或喜,或荒凉。但这种情感无法用言语形容,它就是情感本身,一种共通的能量。因为情感,ta们彼此遇见,又彼此陌生。所以,您的电影似乎在描绘一群散落的人物,但ta们其实在一个共同的结构中结合在了一起。
是的。我最早写完剧本,第一个看的人应该是王晓振(在影片中主演了第三段故事),因为我们交流比较多、也比较直接。他当时就说这三个故事很有趣,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一个整体。那时我也在纠结,这三个故事是否统一,会不会显得割裂。
这个剧本是在封城居家那个阶段一气呵成写完的,所以它不是短片合集,而是一个中长片的结构,几个人物无法完全割裂。我也想过,单独剪出一段故事能否成为一个短片,后来发现不太适合。这几个人物需要有相互的化学反应,才能传递出一种完整的情绪。
起初我并没有想做任何串联,每个故事都更独立。为了让演员们理解这种三段式结构是成立的,我给ta们看了一些参考影片,比如凯莉·莱卡特的《某种女人》[Certain Women, 2016]。又比如深田晃司的《东京人间喜剧》[2008]这样的作品也会通过一些细节,比如电视新闻,来建立联系。让ta们三个人在夜晚同时醒来是我后来才有的想法。我也经常在夜里被外面的垃圾车或扫雪车的巨大声响吵醒。半夜醒来时的情绪,不是简单的忧郁或悲伤,而是一种放空,仿佛时空被调换和搁置了。所以我想,这三个素不相识的主人公,或许会在同一时刻醒来。就像我们有时刷朋友圈,会发现有朋友也在这个时间醒着。我想营造的就是这样一种时空氛围。
拍第一个故事时,剧本里并没有写这个。但当我看到演员于宝坤喝水的背影,觉得那个画面很有感觉,于是就想拍一下他起夜喝水的场景。喝水这个动作,我觉得和吃饭一样,都很有意思。在特别安静的时候,这些动作会被放大。人需要进食,独自吃饭,在我看来是一种摄取的过程。当一个人非常不想动、非常无聊,或半夜醒来非常孤独时,他依然需要为自己服务,比如喝水、进食,这些行为反而更能凸显一种孤独感或无力感。于是我拍了这个动作,后来觉得每个主人公都应该有这样一个时刻。

包括第二段里李可[陈宣宇饰]半夜起来的情绪,她表演时其实非常强烈,眼泪清晰地流了下来。但后来我把流泪那段剪掉了,只用了前面的部分。我觉得流泪的情绪太强烈了,我不想要过于激烈的情绪,所以都收了一点。这可能也是导致观众不易进入的原因之一,电影里没有太多特写,或者更戏剧性的东西来引导观众。我的创作好像很多时候都是不让观众轻易进入,有点像是“你先来看看”,但看完之后我又会把你推开。

您似乎很关注人物的日常动作,并把它们串联起来。比如徐博准备出门时穿衣、穿鞋、拿排骨,李可也有翻行李箱的动作。
你说的这个我想起来了,其实每个故事的人物小传和背景都挺丰富的。我不能只让演员去表演这些动作,ta们需要一个信念感和背景故事来支撑。比如李可这个角色,我最初的设计更复杂。因为资金有限,我不想进行太多复杂场景的拍摄。我曾想过拍朱老师去药店买药,因为他睡眠不好;也想过拍李可的妈妈,她是一个上夜班的人,会在早上给李可准备好饭菜再睡觉,而李可可能昨晚在客厅看电视睡着了,早上起来看到饭菜时,妈妈已经睡着了,两人总是错过;我还设想过李可去联系李可如的过程,她可能是通过一个在当地开店卖货的小学同学,问到了李可如的微信。但这些后来都省略了。如果拍出来,故事可能会更完整,但也许就不那么零散了,而会更像一个传统的长片。那样的话日常感会更突出,但我还是想捕捉这种动作性的、日常的瞬间。
这可能源于我平时会注意到很多微小的细节,比如小虫子或者石头。因为对这些细微事物的察觉,我才会关注到一些有趣的动作和时刻。我特别喜欢《永远超级幸福》[SUPER HAPPY FOREVER, 2024],五十岚耕平的电影我都看过,包括《吾泳之夜》[泳ぎすぎた夜, 2017]和之前的《屏息如爱人》[息を殺して, 2014],我都很喜欢。《永远超级幸福》里有一个人手机快掉了,被主角马上接住,那个瞬间两个人因此相遇——我对这些细小的动作很感兴趣。

SUPER HAPPY FOREVER (2024)
对人的观察也一样。我跟演员说,我想呈现的感觉就像是我们在咖啡馆观察邻桌聊天,我们不知道ta们的背景故事,但因为听到了ta们的谈话内容,我们就会对ta们产生一个初步的认知和想象。我想通过人物的交谈和动作,让观众对ta们有一个第一感知,从而去幻想ta们可能经历了什么。比如李可游走、睡觉的状态,她的一些身体动作和情绪,都能让观众去想象她背后的故事。
就像刚刚您所提到的一样,其实我看《梦的拜访》的过程中,有些片刻也令我想到了《永远超级幸福》,但是不是说《梦的拜访》和《永远超级幸福》是同一类电影,只是说这两个电影都关乎于某种已经不可言说的,或者说等待去追寻但无法追寻到的那种强烈的情感。仿佛都是那种人物经历着某些喜悦的事情,但其实ta们还是相当悲伤。ta们是处于两种相反的情感中、被两种相反情感被迫夹着的人物,就好像生活在平流层里面,被两种云所怀抱着,被两种心情所簇拥着。您在写作这些人物的时候,有考虑让这种心情始终伴随着人物吗?
确实在写的时候我就希望这种心情能伴随人物。我也给朋友看过剧本,有影片的演员王晓振,还有比如《星溪的3次奇遇》[2018]的导演竹原青——我们当时是通过写影评建立联系的。我当时喜欢写一些小故事,她很感兴趣,我写了就会给她看。她看了剧本之后觉得故事里的人物就很像我的日常,但也指出了一些问题,比如人物情绪可能太同质化了,如果有一个或几个人物的情绪不一样,会不会更好看。
我也思考过这一点。比如李可如和朱老师这两个角色,我最初是想让ta们与众不同的。朱老师这个角色,我曾跟另外两位当地的演员搭过戏,其中一位的表演更戏剧化、更影视化,但我不想让作品的气质因此被冲散,那样就很难再拉回来了。所以我希望朱老师的扮演者更当地、更融入。因为东北人真实的一面,有时话会更多,ta们的忧郁往往是在大量的调侃、聊天、吹牛之后那个安静的瞬间。我最初想达到这个效果,但可能能力有限,当时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好好呈现。
第三段可能有点这个意思,在大量对话中营造一种沉浸感。第二段我也想让李可如这个角色跟李可有更多区分,设想她是一个非常开朗活泼、穿着皮衣带李可到处玩的女孩。但后来没找到合适的朝鲜族演员,时间又很紧张,要在二十天内拍完。最后找到了南方的演员何佳慧,她给我的感觉很素人,虽然已经演过了一些电影。我想顺着她的节奏和表演方式去调整。结果发现,这几个人物的性格好像又变得差不多了,区分度没有那么大,而是变成了一个人物撬动另一个人物的故事。比如,通过李可如的处境来反映李可未来可能面临的困境,通过松松的处境来反映老王。最终,大家好像都差不多,都活在这样一个空间下。

李可如(何佳慧)
这可能也和我的气场有关。我身边的朋友性格各异,但在剧组里,我当时的气压也比较低,不是那种很高昂的状态。好在我的执行导演,也是我的师弟,他对片场充满激情,能帮我调动一些情绪,这都是一种互补和帮助。
我发现在《梦的拜访》里面很多人物的语调都是很强烈的,但是ta们也有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朱老师这个角色,他其实在戏里面相当于是徐博的另一个父亲。我特别喜欢朱老师的表演,他的语调非常特殊。因为语气总是关乎于ta们的要讲述的自己的故事,我想知道你在拍摄的过程中如何与这些演员沟通并协调ta们的语调和语气?
其实我对每个演员说得都不是特别多。说实话,当我自己不是很清楚的时候,我不想扮演一个指导的角色。这三组演员都曾有过疑惑,不知道我到底想要什么。比如陈宣宇,拍了一小半之后,她还在问我想要的所谓的“down”的情绪具体是什么样的,因为她觉得“down”有很多种。我其实也描述不好那种“down”来源于什么,可能宏大一点说,是那种日常感、宿命感的东西,它可能是毫无缘由的。但我能确定的是,她之前的表演状态是对的。
关于语气,我跟朱老师[袁利国饰]聊过,他说他在看过剧本后也想往洪常秀电影里人物的感觉去靠。袁老师之前出演的都不是这么文弱的角色,他认为我这部戏是他演过最文艺的。所以他会故意压低语气,让自己显得像个老师。我给他的人物背景是:一个曾经的理想主义者,可能在学校和年轻的实习老师出过轨,后来离异,又因为一些事被举报,最终没再当班主任,也没再写小说。这个背景是为了让他能进入那样的情绪,所以他的说话方式才是那个样子。

朱老师(袁利国)
于宝坤[饰徐博]是唯一一个我没有给太多资料的演员,因为他是我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是唯一的学院派。我觉得他的状态本身就很好,就让他处在那个位置去自然发挥。表演系的同学也有个特点,为了塑造角色,他在拍戏前会控制饮食,一天不怎么摄入碳水。所以他进组后一直处于一种挺低沉的状态,也没什么力气。为了拍好睡眠的戏,他会刻意前一晚不怎么睡,第二天拍戏时刚好能进入那种困倦的状态。我发现演员对于表演的信念感非常强。睡眠这件事,在我们看来可能就是躺下闭眼,但他们一定要让自己真正进入困倦的状态。包括第一段里饭店老板睡觉的戏,他也是真的快睡着了,所以语气也会改变。至于陈宣宇,我看过她演的其他方言电影,但因为她是我老乡吉林人,我就想让她说吉林话,感觉很亲切,像我的小学同学。

徐博(于宝坤)
我不会给ta们任何压力,在现场我把自己放在一个隐秘的位置。现场没有监视器,一开始有个小的,后来坏了。起初我还看摄影机回放,后来索性就看现场,有一种业余感。这样演员也没有压力,不会总想着自己的表演导演是否喜欢。我想把这些压力都拿掉,让ta们有日常感,自由一些。当然我也会把握一个度,不能太随意,会用写好的台词把ta们收回来。比如茶馆那场戏,两个女孩聊天,拍了三四条,每条版本都不同,但我要求一些关键元素必须要说到。
第三段的故事完全是即兴的,所以ta们的语气就很日常,就是聊聊天,没有特意控制。但我有跟ta们说要放慢语速,多一些停顿。我跟王晓振也聊过,我很喜欢让人物慢一点说话。这可能有点形式感,比如我甚至会给袁老师标出哪里需要停顿一下。有时候感觉不自然,但我就想要那个停顿。王晓振也建议我回头可以总结一下为什么喜欢这种停顿,思考一下它能否成为一种系统的风格。
您提到监视器损坏,让我想起阿尔伯特·塞拉,他拍电影时常拒绝监视器,甚至有时会背对拍摄现场,说只听声音就够了。
我没看过他的访谈,但我拍的时候确实有这种感觉。拍到后面,演员在前面表演,我蹲在地上看地面。那一刻我在想,我是在干嘛呢?感觉我像在祈祷,祈祷某些时刻的发生。这个电影里面很多都是我在祈祷一些时刻发生,比如说下雪。其实一开始我会让演员也有一些祈祷的动作,后来删掉了。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习惯,有时候会睡着睡着就起来,因为我想到一件事,就是想起来拜一拜,感觉这是在表现自己的情绪。后来我发现洪常秀的电影里面也有这个,比如《引见》的片头。这其实是一个挺日常的动作。
监视器的存在是做什么用的,我其实也不太清楚。它可能会让画面布置得更好,但那是一个更工业化的做法。我之前拍过一个创投给了十万块的短片,九分钟,两天就花超支了。我就想,这个钱完全可以拍个长片。那时有监视器,但我也很少一动不动地坐在前面,还是会在现场来回跑。我觉得可能只有当你更有目的性、更工业化时,你才知道监视器传达的画面是对是错。但我觉得看现场挺好的,像拍胶片一样。很多戏一两条就过了,抓一些即时性的东西,看看现场表演,再简单看一下回放,我就很满足了。

我也喜欢拍完后把素材放一放,让它发酵一段时间,可能会自己产生一些灵光。我回避即时去看,就像我不喜欢看自己写过的东西一样。所以监视器这个事也是如此,确实有些时刻我没有看画面,只是听听声音,后来看回放觉得没问题就行了。当时演员也会质疑,觉得我可能太拘谨、太客气,不好意思麻烦ta们多来几遍。正常情况是导演拍很多条,演员拍到腻。在我这里相反,演员会说:“导演,如果你不满意我们再来一条。”但我会想,一是时间有限,二是我觉得它其实就是那个样子,再来很多遍也会消磨掉最初的感觉。
《梦的拜访》首映后,有一些批评的声音。我想在这个节点直接地问您:您介意有人将您的电影评论为一部“洪常秀式”的电影吗?
不介意。每年都会有很多电影被形容为像洪常秀,或像其他导演。因为电影就像人,我们可能就是属于思考同一类问题的那一类人,像莱卡特、五十岚耕平都是我很喜欢的导演。我们这一代导演无法排斥被影响,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影迷。
不像以前,电影必须在电影院看。现在你喜欢这个东西,你就会大量地去看。很少会有人完全不看电影就去做电影,那种天才应该会很少。大部分人进入这个行业必然会看很多电影,我觉得电影已经变成了一个世界,一个能量场,你无法排斥潜移默化的影响。电影的生产也陷入了一个循环,只是因为每个人都不同,所以会产生很多不同的作品。
会有一类人,就像朋友一样,待在一起觉得舒服。我们都有过这种经历,跟某些人在一起就是不舒服、想回避,电影也是这样一个能量场。所以被评为什么样式我觉得无所谓,可能只是大家想到了这些人,用ta们来形容,贴上一个标签。但我肯定无法碰瓷这些大师,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只是在刚开始创作时可能会有一些痕迹。
虽然我觉得确实某些时刻会令我们想到洪常秀的电影。比如有个镜头是李可提着行李箱经过徐博身边,徐博靠在墙上抽烟。然后有个突然的、非常简单的音乐,一个变焦向前推的镜头。那时候确实捕捉到了《草叶集》[풀잎들, 2018]的某种精神,因为音乐连接了我们共同的情感,或者说音乐是我们所有故事性串联起来的唯一的理由。

但是在我眼里,您还是您自己。我们现在要谈到您的场面调度问题,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您的场面调度甚至影响了您所有的文本和故事。首先您的调度总是关于某种“分心”。比如说您在拍摄两位演员对话的时候,会突然拍摄到世界其他角度。有一个镜头印象我很深刻,就是朱老师在吃饭的时候,他跟徐博打电话,你会拍摄厨房的师傅在炒菜。厨房的师傅是一个其实不太重要的角色,但是你依然会拍摄他,这让我很惊奇,让我意识到这个电影的每个人都如此的重要,他的劳动闪耀着他的光辉。
还有一点是您会摇动摄影机。结尾的镜头中,人物先是走出了摄影机,紧接着摄影机摇跟上他,仿佛是某些东西在试图抓取、跟随这个人物。这点对我来说便区别于其他作者,这是您自己的东西,您开始尝试在场面调度上作为作者深耕影像。所以我想知道在场面调度的层面,或者说我们用更理想化的词语——“这种写作”,您是如何考虑的,在影像之中您想注入怎样的理念?
其实很简单。我开始做这些摄影机运动,是因为我用的就是一个大学时的旧脚架,它上下摇动时很顺畅。摄影机是借的朋友的索尼FS5,我自己也有一台佳能XA40,后来发现洪常秀也在用这台机器,当时还觉得很巧,很兴奋。电影里补拍的雪景就是用我自己的机器拍的。我很喜欢在电影里加入一些我自己拍摄的、而非完全由摄影师掌控的画面。
你提到“分心”,这和“散心”有点像。我一直想做一个叫“散心电影”的工作室,甚至想做“散心影展”。我觉得这个词可以概括很多我喜欢的创作者的感觉,有一种让人分心的特质。我想让观众既能进来看,又想把ta们推开,让ta们离远一些看。
拍的时候我有这个感觉,但有人会觉得这样更像洪常秀了。其实这并非刻意设计,我只是拍了一些这样的镜头。比如有一场李可前男友出现的戏,我用了一个360度的摇镜,他出现后又消失了。那个调度挺有意思,但后来没放进来,因为不想显得太炫技,而且那个场景的蓝色栅栏不好看。我做的调度都很日常,是在三脚架上就能完成的,而不是靠摇臂等复杂的设备。这种日常感的东西,有时能带来神奇的时刻。
总的来说,我拍的东西还是偏平面化的,因为我当时想的就是写作,像小说一样把故事呈现出来。我现在也在思考调度,希望后面的片子能有一些更精致、更好玩的日常调度。比如片中的自动推拉门,写剧本时我就想要一个自动门,不想让演员去做推、拉这些多余的动作。很神奇的是,我找到的那个酒店刚好有自动门,还有一个升降梯,这就形成了一种横向和纵向的视觉调度感。所以平面之中也是有调度的。

您似乎很熟悉自己手上的机器。戈达尔、洪常秀、刘伽茵,还有潘佩罗小组等等这些我们所推崇的作者,在ta们低成本的创作中,很多都是导演自己掌机,ta们是最熟悉自己手中机器的人,最清楚自己的机器能拍出什么样的影像。
我不太确定。我只对自己用过的机器有所了解,对很多专业设备并不熟悉。每台机器都有自己的小问题,比如冬天会掉电快,对焦也会受影响。但我自己的机器拍出来的色彩和感觉,我觉得是好的。可能因为我是东北人,我也常扛着机器或脚架自己去拍雪景;后面有一些我自己记录的景色,有点你说的对机器很熟悉的感觉。我很喜欢俄罗斯导演瓦迪姆·科斯特罗夫[Vadim Kostrov],他用小机器拍了很多纪录片,我很喜欢他拍的景。《梦的拜访》里,朱老师和徐博聊天时插入的岛上画面,还有一些雪景,都是我后来自己扛着摄影机去拍的。我很享受那种创作时刻,有点像画家拿着画笔和画架去写生,是一种纯粹的记录。

Normandie (2024)
关于景观,第二段故事里,李可和李可如因为蓝色栅栏的阻挡,要找一个高地用望远镜望向朝鲜。这就像两个场景、两个景观在互相望向彼此,与她们彼此梦到对方形成了呼应。三段故事对梦的思考不仅体现在梦的内容不同,更体现在对梦的“写作”态度完全不同。
是的,我有意地区分了三个梦的表现形式。第一个梦很平常,一个东北边缘的人梦到海,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设定太普遍、太简单。但在那个地方,回到家,就会觉得这件事并不虚构,它很日常。
第二段的梦,是两个人彼此梦到对方,相互交集。这更像是我编织的一个文本性的梦。很有趣的是,电影放完后,没能来现场的演员何佳慧告诉我,她前几天梦见了陈宣宇。我选何佳慧也是觉得她身上有些神奇的时刻。我记得她当时去演茶馆那场戏的时候,我觉得她穿的那件毛衣挺好看,她说这是她去一个过世的亲戚家里时,人们发现这件衣服跟她很适合,就给她穿了。
第三个梦,更现实,也更恐怖和宿命。你会梦到一个已经死去的人,但你不知道他死了,醒来后才发觉。我想把这三个梦处理得有层次和递进,让它成为一条重要的串联线索。
第三段故事里的梦,让我想到了加瑞尔的《北斗七星》[Le grand chariot, 2023]。但您的处理和加瑞尔是相反的。加瑞尔是让我们先知道父亲死了,再看到他的身体出现,从而感到惊奇。而您的电影里,我们先看到一个老人出现,感觉他很陌生、很奇异,直到后来老王打电话,我们才知道那是他已故的老舅。这时情感才被串联起来,我们才重新思考之前的镜头。对我来说,您的电影比起洪常秀,其实更像加瑞尔。就像加瑞尔的电影总是研究人的“出现”,您的电影总是在研究人如何“退场”。

Le grand chariot (2023)
谢谢你的反馈,这确实帮助我思考了一些问题。第一段是李可的离开,第二段是李可如的离开,第三段是老王的退场,这种离开、退场的情绪确实很触动我。加瑞尔的片子我也看过一些,很喜欢,但看得相对少,可能后面会再多看。大舅那个时刻,他们穿的中山装也带有一种对过去年代的回忆,既有亲情,也有一种恐怖感和宿命感。我当时还想过在背景中放一些那个年代旧电影的隐隐约约的声音,不过后来想还是无声吧,但是那一段是想要表达一些时代的宿命感。
观看《梦的拜访》时,我能深刻感受到您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尤其是第二段故事,李可和李可如是多年未见的小学同学,重逢时彼此都怀着善意,祝福对方过得好。这种对人物关系的善良祝愿,贯穿着整部电影。我们小组有位成员形容您的电影很“清新”,她觉得其中的男性角色几乎没有给人一种油腻的感觉。
我想起以前写影评时,也有人说我带有一种善良的道德感。确实,我对很多电影都很包容,但涉及到某些道德问题时会比较应激,甚至会打一星。因为我觉得影像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有些电影传递的东西,我觉得是不道德的,是邪恶的。比如有些作品非要把一个男性角色写得很坏,后面再让他变好,我觉得这种戏剧性的反转在现实中很虚假。
至于善良,可能因为我情绪比较平稳,所以人物也显得如此。我记得侯麦的《冬天的故事》[Conte d'hiver, 1992],最后让女主角又见到了她曾经的情人。我当时就觉得这非常善良和美好。现实中很少有这样完满的结局,但侯麦愿意去呈现它。很多电影可能会因为所谓出轨或者婚外情是不符合社会道德的,就批判这样的女性,但侯麦没有,他让她显得很善良、很美好。你刚才说的,让我想到了这一点。

Conte d'hiver (1992)
您是第一次来西宁吗?
不是,我来过好多次了。十年前我大学时在这里做过志愿者,后来做过短片预审,也作为媒体来过。但这次感受很不一样,因为是带着自己的片子来的,会更紧张一点。
您如何看待西宁这个空间?如果在这里拍一部电影,您会如何构思?
我外公刚毕业时曾被分配到西宁的小桥医院工作,一个东北人来到这里,我觉得挺神奇的。我本来想去拍拍小桥医院和一些街道,觉得或许能和我其他的镜头产生串联。昨天我在车上看到两个穿着西北特色深色衣服、戴着白帽子的老人,在城市里散步聊天,那一瞬间我挺羡慕的,感觉他们很有故事。西北的城市,高原、开阔、清爽。但具体拍什么空间还没想好,只是不想重复那些在别的西北电影里看过的场景。
从您的谈话中能看出您对景观的看法,您似乎倾向于拍摄旅途中的、而非身边熟悉的事物。
也不尽然,它们其实也是我熟悉的空间。我现在在杭州生活,对那个城市我一直在摸索。我去一个城市,是想找到一种感觉。我不会看到一个景物很有意思就马上去拍,而是要等我反复看过很多次,对它慢慢有了感情之后,我才会去拍它。比如我曾拍过同学家楼下的一个景,一个露出尖顶的楼和几棵树。我对那种小景很感兴趣,因为它承载了我的情感。我上学时常去他家,总路过那里,以后那也会是他大半辈子回家时会看到的地方。它可能不起眼,但因为有感情,我才会拍。


《梦的拜访》取景地
我们“异见者”团体也自己创作,在评论和创作的实践中,我们发现评论能让我们更接近作者的精神,从而在自己的拍摄中,不知不觉地掌握了那种精神,这是一种避免表层模仿的学习方式。很多对《梦的拜访》的评论,简单地称之为“洪常秀式”,这让我们非常不满,因为他们只看到了表层。我们认为,您和洪常秀的精神关联在于对“言语交锋”的探讨。您和我们的立场是相似的:都进行过评论,都对表层不感兴趣,而是研究前辈的精神,并用自己的精神去逐步“侵蚀”它们。
我觉得我们的过程可能有些相近。我做的这些事,无论是策展还是其他,除了维持生计,核心都是在吸取一种电影的精神。做评论确实能帮我们梳理和发现自己被影响的脉络。但我也不希望完全从一个影评的视角去做创作,它还是要基于我的生活体感。我还是挺喜欢亲自去体验、去熟悉、去了解一个地方,一个事物。
能否透露您下一部作品的计划?
我没有特别明确的计划。之前写过几个剧本,不再是现在这种零散人物的结构,但我发现我还是挺喜欢这种人物间相互作用的感觉。我现在更想写几个小说,或者做一些记录性的东西。比如拍一些夜晚工作的人,或者拍人吃饭,但会更艺术化一些。我也很喜欢收藏家庭录像带,对声音媒介也很感兴趣,想做一些传达记忆和情感的小片子。
至于故事长片,目前没有特别想拍的。电影太麻烦了,要么有创投的钱,要么就很难进行。如果拍出来自己都感觉不到激动和兴奋,那我可能就先不做了。
那么假如您再拍摄下一部,您会期待是一种风格的转向还是延续?
我觉得大概率会是延续的,因为都是从我个人出发。我很想拍一些我们原来不熟悉的群体,我现在很想了解ta们:八十年代的电影里,我们还能看到公交车售票员、科学家的故事,但现在的电影里,这样的人物消失了,可能连服务员的故事都没有。我很想为这些人拍一部电影。但风格上,我相信会是连贯的,因为我吸收的东西已经内化了。
我一直没觉得这是我的“第一部作品”,这个词听起来太重要了,好像是酝酿已久。但其实我的创作更多是即兴的,我知道我要去做,做完了怎么样,没有过多想法。只是想给帮忙的朋友们一个交代。我最希望看到的观众反馈,是ta们看完后能想到自己的生活。上次放映后有个女孩说,感觉电影里的对话和她平时的想法一比一复刻。这正是我创作时想要达到的——希望能有人在偶然间看到这部电影,产生共鸣,觉得“这一段刚好和我的经历一样”。
这就是您的电影想要达成的核心目标吗?
对,就是想被偶然地看到,偶然地被喜欢。我以前淘碟,就是看封面或剧照来选电影,有时会淘到完全是我的菜的作品,例如《水瓶座》[Aquarius, 2016]和《舍间声响》[O Som ao Redor, 2012]的导演小克莱伯·门多萨[Kleber Mendonça Filho],他其实就是我看碟片看到的。我很怀念那个时候,所以也希望我的电影能零散地被大家看到。如果某个人的情绪刚好匹配上了,ta看了觉得和自己的经历很像,我就会觉得很幸福,这就挺好。
感谢您。刚刚您提到一句话,我突然想到,可以直接拿来做标题,我觉得非常美——“被偶然看到”。
FIRST当时让我写导演阐述,我写的就是,想要做那种“被偶然拾得的电影”。


全文完
/TheEnd/
这是一条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