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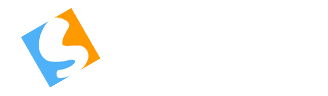

2025年暑期档,一部以南京大屠杀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影片《南京照相馆》上映28天票房已近27亿元,并引发广泛讨论、产生较大影响。它的成功,绝非简单的市场策略胜利,而恰恰印证了其内容之深刻,精准地回应了当下中国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对民族历史一种日益增长的、具身化的认知渴望。人们不再满足于教科书上抽象的叙述,而是渴望触摸历史真实的肌理。这部电影恰逢其时地提供了一座桥梁,它通过一个极具悬疑感和人性张力的故事,引领观众进行了一次直抵民族记忆神经末梢的“媒介考古”探险,实现了艺术价值、历史价值与公众情感共鸣的多维统一。
1938年,在今天南京市估衣廊附近的华东照相馆内,15岁的学徒罗瑾在冲洗日军军官送来的胶卷时,发现其中记录了大量暴行画面。他冒险加洗30余张照片,精选16张制成相册,封面绘有滴血的心脏和“耻”字,以留存罪证。相册几经隐藏,后因罗瑾被迫离开南京而遗失。1941年,罗瑾的同学吴旋在毗卢寺发现相册并秘密保存,直至1946年将其提交给南京市临时参议会,这份浸染着鲜血与勇气的“京字第一号证据”,成为审判战犯谷寿夫的关键证据。这本相册不仅见证了两个普通中国人的勇气,更以物质形态承载了无法磨灭的历史真相。它的传奇命运使得这段充满伤痛的历史记忆不再仅仅是文本的、叙事的历史,更是由物体、技术及其物质性实践所构成和传递的历史。
电影《南京照相馆》正是以这一真实历史事件为蓝本,将叙事聚焦于一家名为“吉祥”的照相馆内普通百姓冒死保存罪证的故事。片中,邮差阿昌为躲避追杀而冒充学徒,在冲洗底片的过程中意外揭露日军暴行的铁证,并由此完成了一场从只求自保到坚守真相的灵魂蜕变。通过这样的艺术处理,罗瑾与吴旋的真实事迹被赋予更为宽广的群像生命力。影片引领观众越过表层叙事,直接触摸历史得以传承的物质筋骨与情感血脉,完成了一次直指“深层时间”的媒介考古。
01
媒介考古:相册中的历史记忆机制
《南京照相馆》在如何书写和传承抗战历史方面,进行了一次基于“物质性转向”的可贵探索。在“万物皆媒”的今天,我们愈发认识到,媒介绝非透明的信息通道,其物理形态、技术特性(即“物质性”)深刻地塑造着社会历史文化的建构方式。传统历史研究常将档案视为中性的信息载体,聚焦于文字记载的“内容”。而历史学的“物质性转向”则迫使我们关注档案本身的“物性”:它的材质、形态、制作工艺、流转轨迹,以及它如何在与人的互动中能动地塑造历史进程。
“京字第一号证据”相册的制作和流转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壮举:罗瑾的加洗、挑选、装订、绘制封面,是将无形的、流动的集体创伤固定化、物质化的过程。封面上的“心”与“耻”绝非简单装饰,而是将内在的情感痛苦外化为可见、可触摸的符号,使相册从一个被动的记录工具升华为一个主动的、殉难式的纪念碑。它的隐匿与流转——藏于墙缝,匿于佛座——则生动揭示了在极端暴力下,物质载体如何成为信任、勇气与记忆的实体化交接棒。它的每一次易手和隐藏,都在地理空间上刻写了一条秘密的记忆路径。最终,它在军事法庭上的呈现,其无可辩驳的证据威力,远胜于单纯的口述。它不再是被动的“物”,而成为主动介入历史、改变审判走向、推动正义实现的关键行动者。
《南京照相馆》精心重构了20世纪30年代的媒介生态:以照相馆作为现代性技术空间,暗房作为显影真相的隐喻场所,照片作为高度写实的视觉证言——共同织就一套“媒介记忆装置”。观众不仅见证历史,更理解记忆得以生成、保存与传递的物质机制。影片还借由德国媒介理论家齐林斯基(Siegfried Zielinski)提出的“深层时间”的视角,打破媒介进步主义迷思,揭示影像技术内在的断裂与矛盾。它犀利地指出摄影自始便被植入的暴力基因:通过蒙太奇将日军记者按下快门与士兵扣动扳机的动作同构,深刻呼应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拍摄是一种象征性谋杀”的论断,迫使观众直视摄影背后的权力政治——从取景的裁切、快门的掌控到显影的抉择,无不渗透着视觉政治的操演。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影片通过并置日军“亲善”摆拍底片与在暗房中逐渐显影的暴行图像,实现了一种媒介自反:它不仅再现了历史,更将摄影技术本身推上审判台,剥除其“客观记录”的光环,揭露其既可遮蔽亦可揭示真相的双重性。在这一过程中,媒介不再是中性的容器,而成为历史真相与权力操控交锋的战场。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南京照相馆》的价值已远超艺术范畴,它深刻洞察了历史记忆的机制:既揭示了档案作为“对抗遗忘的武器”的本质,也暴露了影像在权力博弈中既可遮蔽又可揭示真相的双重性。影片也尖锐地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媒介如何实现从统治工具到解放武器的转化?日军用相机制造谎言,实施视觉殖民;而影片主角则挪用同一技术,将相机和暗房转化为守护真相的堡垒。这种转化依赖于人的勇气与伦理选择,也基于对媒介物质性的深刻理解。而《南京照相馆》正是这种“转化”在当下的延续——它将历史中的传统媒介——照片,转化为另一种新的媒介——电影,完成了一次跨越世纪的媒介间性实践,实现了对抗历史虚无主义的媒介接力与共生。
02
记忆重构:从民族创伤到世界遗产
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以立法形式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以此缅怀所有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2015年10月9日,《南京大屠杀档案》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标志着这段历史被确认为全人类共同的永久记忆。而“京字第一号证据”的非凡旅程——从罗瑾私藏的简陋相册,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关键物证,再到成为世界记忆遗产的核心组成部分——正是一段民族创伤记忆获得升华,并被赋予全球意义的象征过程。国家公祭与国际认证的顶层制度架构,为流动易逝、代际更迭的社会记忆提供了法理依据和仪式框架,使其得以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实现稳定化、常态化的传承。
然而,所有这些宏大叙事和符号建构,都深深植根于那些原始、粗糙、浸满创伤痕迹的“记忆微屑”。正是这些微小、脆弱却坚韧的物质碎片——一本相册、一张底片、一页日记,承载了历史现场无法篡改的“在场性”,为集体记忆的建构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证据和情感依据。这表明,集体记忆的形成绝非简单的自上而下的灌输过程,而是一个从微观物质实践到宏观符号体系不断辩证互动的复杂网络。
《南京照相馆》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将严肃的历史反思,不着痕迹地熔铸于一个充满戏剧张力、情感浓烈的影像叙事中,让观众得以直观地“触摸”历史。它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历史绝非故纸堆中冰冷的文字与年份,而是由无数曾饱含生命温度的物质痕迹所承载的与我们血脉相连的活的经验。影片最动人的时刻莫过于结尾处:当1937年的断壁残垣与今日南京璀璨流动的都市盛景,在银幕上叠印、渐次交融,这一刻,胶片彻底超越了其作为历史物证的静态功能,过去与现在进行了一场无声却震撼人心的对话。似乎在昭示我们,今日我们所享有的和平与繁荣,并非历史的必然结果,而是由无数个“罗瑾”与“吴旋”在最为黑暗的时刻,凭借近乎本能的勇气、沉静的智慧乃至生命的代价,顽强守护住真相的火种换来的。这本相册的传奇,以及电影对其的再现,印证了影片主角阿昌在暗房冲洗罪证照片时的独白:“照片能褪色,但历史不会——它只是等有人翻开。”由此,每一张得以幸存泛黄照片,都不再是静止的过去式,而是投向时间长河、等待未来某一时刻被接收、被解读、被回应的永恒信标。《南京照相馆》也因此既是一次历史的回溯,也是一次未来的播种——它提醒着我们,在万物皆媒、影像泛滥的今天,守护真实、传递记忆,仍是一种必要的道德实践。
(作者系中国电影博物馆研究部负责人、研究馆员)
文 /刘思羽
编辑/吴嘉怡
责编/杜思梦
CONTACT US

转载授权 | 3117342843(微信)


投稿邮箱 | zgdybxmt@qq.com
MORE NEWS
© 中国电影报原创稿件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欢迎分享至朋友圈
这是一条公告